商業和技術是兩回事。一種商業模式之所以存在,必然有其道理。在商業模式存在的土壤沒有變化的背景下,單單指望一個技術標準改變行業的商業模式和市場格局,無異于緣木求魚。
在美航的NDC之亂之后,土耳其航空又站出來挑戰GDS系統:土耳其航空在今年5月發布了自己的TKConnect NDC平臺,并從10月1日開始收取GDS附加費。
我個人認為這次挑戰,十有八九會正如之前美國航空的例子一樣無果而終:為了闡明這個邏輯,我們首先要理清航空公司、GDS、代理人、OTA和旅客五者之間的關系。
在這五者當中,代理人是出現的最早的。
早在18世紀,就有人做著旅行社這門生意,幫人代訂船票和客棧了。美國運通在1915年開始涉足旅行業務,而中國第一家旅行社,則可以追溯到1923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旅行部(今天的中國旅行社)。
最早的旅行社,往往都和銀行緊密綁定——這是因為他們與其說是旅行社,不如說更接近于今天的商旅公司。
在私人金融還不發達的20世紀,為了避免攜帶大額現金旅行,商人往往會在銀行存款并開具記名支票隨身攜帶,以防路上不測。
考慮到銀行的使用場景和旅行緊密綁定,對于銀行而言,旅行社業務因此是個不錯的順帶差事——直到今天,不少銀行仍然在為高端卡持卡人提供旅行社服務(例如運通針對個人卡持卡人的Amex Travel和針對公司卡持卡人的Amex GBT)。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旅行社等代理人,尤其是TMC,往往有自己的穩定客戶——這些客戶不是「航空公司的客戶」,而是「代理人或TMC」的客戶。
我們把事情說回航空公司。
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最開始的時候,航空公司是直接向旅客售票的。這一模式一直持續至今,旅客現在也可以在機場的航司柜臺買票。
雖然如今大概只有千分之一左右的旅客,會在機場現場買票,但是這種模式其實是客票變更(改簽、退票)等場合的大頭(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自愿退改簽,是在機場柜臺處理的),加上要服務非自愿退改簽,因此倒也一直存續至今。
甚至乎有一些票只能在機場購買——例如下面的這張空席候補票,就是在深圳機場的東航柜臺現場出票的。

當然,到了機場再買票顯然有買不到票的風險,總有旅客希望提前訂票。但是如果提前訂票還需要跑一趟機場,那就太辛苦了。
因此,一些生意比較大的航空公司,還會在市區開設「售票處」方便旅客——例如南航在廣州的市區售票處開在廣州火車站旁邊;深航在深圳的售票處開在農林路鑫竹苑。
但是,對于航空公司而言,自己開鋪頭售票有兩個問題。鋪頭的租金是固定成本,每個月實打實地要花出去的。
這使得售票處不可能開得太多(大部分城市只有機場一個,只有樞紐城市或者極為重要的城市才能有市區售票處),影響了航空公司接觸顧客。
因此,一些航空公司開始提供電話訂票——旅客打電話訂座之后,或者留信用卡信息,或者在機場給錢。這樣就不用給租金了,但是還是要給工作人員開工資,還是固定成本。
現在打95583、95530和95539,還是可以訂票的——工作人員會給你發一條短信引導你支付。
這個時候,航空公司就想起了它們的前輩——船公司和鐵路公司。
對于船公司和鐵路公司而言,旅行社是一個隨叫隨到的銷售:由于按單付傭,船公司和鐵路公司得以將銷售成本從固定的租金和工資變成浮動的傭金,大大降低了擴張門檻;甚至乎還可以發揮市區售票點方便的優點,將傭金轉嫁到消費者頭上(例如購買火車票的五元手續費)。
因此,在大部分的時間里,“請代理人代銷”才是航空公司客票銷售去化的主旋律。
互聯網和電腦的發展,使得業界或多或少開始注意到數字化。以前直銷客票需要工作人員和租金,現在只需要花點電腦錢了。
一方面,航空公司也開始在網上銷售客票(官網、小程序、APP都在此列)。另一方面,一部分代理人也將客票搬到網上賣,形成了OTA。至此,五個環節都或多或少地搬到了網上。
有些航空公司就開始打起“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的想法——我能不能把中間商踢了,減少環節呢?有些航空公司就真的開始干。
航空公司一開始想把中間商全部踢了,直接和消費者做生意(純直銷)。這種模式類似于最早在柜臺賣票的時候——只是把柜臺搬上了網絡。在只有一家承運人的時代(例如當年的「中國民航」,或者如今的鐵路),這個策略很有效。
但是,如今旅客一個是講究貨比三家,一個是講究省事。對于使用OTA的價格敏感性旅客而言,放著代理人整理好,比較好的各家航空公司的價格不看,一家一家跑去航空公司官網問價錢?這顯然不現實。
對于使用TMC商務旅客而言,放著每個月幫我開大票,整理報銷單的TMC不用,在官網訂票然后安排秘書打行程單報銷?這顯然也不現實。
對于還在使用線下旅行社的客人而言,放著線下親切的旅行顧問不用,跑去DIY自己操心?這更不現實了,我去線下旅行社就是想找人嘮嗑的,官網我找誰嘮嗑去?
酒店行業不是沒有這樣的例子——現在酒店行業仍然秉持「代理預訂無積分」的原則,希望大家上官網預訂。但是,實際上呢?哪怕是華住和萬豪這樣的大連鎖,還是有一半以上的訂單來自旅行社(包括OTA、TMC和傳統旅行社)。
為什么大家放著積分不要,也要去OTA、TMC?無它,要么比價錢、要么圖省事,僅此而已。
我們接下來把話說到GDS。
航空公司眼看無法消滅所有中間環節直達客戶,就試圖直連代理人,把GDS踹掉。這也就是所謂的NDC。
但是,航空公司沒搞明白GDS存在的目的。
GDS為什么能夠立足?是因為他們能降低航空公司和代理人對接的成本。
眾所周知,兩兩相連節點所需的邊的數量,和節點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一家航司對一家票代簽一份合同,兩家航司對兩家票代就需要四份合同;三三得九、四四十六……全地球的航空公司都想在不同國家賣票,全地球的代理人都想賣不同航司的票。
如果都是雙方協議,那航空公司和代理人維護合同都要累死。
GDS將這件事情的難度,從平方級降到了線性級——你航司跟我GDS簽一份合同,就可以觸達到我已經簽了合同的所有代理人;你代理人跟我GDS簽一份合同,就可以觸達到我已經簽了合同的所有航司。
三家航司對三家票代,現在只用六份合同了;四家航司對四家票代,只用八份合同了。
換言之,哪怕是在NDC架構下,對于代理人而言,和航空公司直接簽署協議也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這個事情和技術無關,純粹是商業和法律上的復雜。
首先,和航空公司簽協議并不能取代GDS,不能說和航空公司簽完就不和GDS續約了——其它航空公司還是需要GDS的。那么,這就使得代理人平白無故多了一筆成本,而且是和售票數量無關的固定成本。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地球上有NDC Aggregator這樣的商業模式:一家公司把各家的NDC聚合起來,提供給代理。這又走回了GDS的老路——當年GDS就是將EDIFACT電報聚合在一起提供給代理,如今只是行業技術升級了一下,商業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改變。
大搞直銷,搞NDC這樣高控制力渠道的航空公司有沒有?有。
我們剛剛提到,GDS存在的意義是簡化代理人和多家航空公司簽單的手續。那么,假如市場沒有多家航空公司,這個前提也就不存在了——反正都只是簽一張合同,要GDS這個中間商干啥?
現實當中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呢?有。這個例子離我們不遠,就在日本。ANA和JAL都是自建渠道的航空公司:JAL有AXESS、ANA有Infini,都是航空公司自己建設的GDS。由于兩者均為自建渠道,因此通過AXESS出的日航票和通過Infini出的全日空票,都是直銷票;事實上,AXESS和Infini作為私有系統,其功能復雜度和性能比EDIFACT要高得多(例如支持兩位字母運價代碼),更接近于今天的NDC。
但是,ANA和JAL可以自己建設GDS的前提,是日本國內的二重寡頭壟斷機制。
日本國內線承運人基本只有這兩家(或者它倆的小弟),同時,日本大部分差旅需求集中在東京(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和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在羽田、成田的覆蓋范圍內),因此兩家公司都可以提供東京往來全日本的服務。
換言之,對于代理人而言,每一家代理人簽兩份合同,就可以銷售全日本的國內客票和大部分(自己公司+寰宇一家或者星空聯盟)的始發國際客票。
兩份合同完全可以接受,因此在日本國內市場存在一家獨立GDS的價值是不大的(也沒有人能擔當這個協調兩大巨頭的和事佬角色)。
但是,全世界像日本這樣,差旅需求高度集中在一座城市,同時民航又雙寡頭壟斷的國家是很少的。中國、歐盟和美國都不是這樣的地方。
就中國而言,我今年上半年和東航打賭,說我可以半年國內出行只坐東航。雖然我的確做到了這一點,但是在航班的選擇上,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掣肘(東航在上海航線上航班量是沒問題的,但是廣州北京航班量就很少了)。
因此,你說下半年我會不會再干這種事,我絕對不會了(事實上下半年我在樂呵呵地坐火車出差)。
國內來看,目前只有大代理人(例如攜程、同程)以「旗艦店」的形式接入了NDC;但是,TMC等真正手上有核心、高凈值客戶資源的代理人接入了多少,則是未知數。
在美國也是同樣的情況。美航之所以會因為NDC陷入「NDC之亂」,根源在于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甚至包括總部所在地達拉斯)等核心大城市的代理的集體反水——畢竟紐約和洛杉磯是美航、達美、聯合齊聚的兵家必爭之地;芝加哥則是上有據守T1的聯合、下有剛剛搬入T5的達美;而達拉斯?別忘了西南航空的總部也在這里哦(笑)。
對于代理人而言,你美航給我臉色,增加我的營商成本是吧?那簡單,「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賣你對手的票不就行了?
聯合、達美、西南三大對手自然也「趁你病,要你命」,臨時加碼了傭金,力求把美航的大客戶挖過來簽協議價。
如此斗爭甚至反映在了機場休息室的人流上;由于這些新協議價普遍贈送休息室權益,因此上半年Polaris和Delta One休息室都是水泄不通,大量企業客戶排著隊拿著協議登機牌進休息室;反過來看,Flagship就有點門可羅雀了。
這件事情最后的收場結局,是以2024年5月始作俑者Vasu Raja的黯然下臺為代價的。
「Others are benefitting from what we’ve done over the last six months. We’ll get that back. I know for a fact we can recapture what we’ve ceded to others」,CEO Robert Isom在投資者會議上對投資者的表述,在筆者看來和公開「謝罪」幾無差別。
我們把視角挪回國際線。土耳其航空面臨的競爭局勢比美國航空嚴峻得多:一方面,印度、東南亞往美洲的市場,也有中東三「壕」、國泰、長榮華航,日航全日空、大韓韓亞強敵環伺。
另一方面,歐洲—東南亞之間,最新加入戰場的中國人在時不時「大放價」(比如同樣是倫敦到曼谷,東航就是比土耳其航空便宜一千五百塊錢)。

在這樣競爭激烈的大環境下,將GDS和代理人推到自己的對立面這一行為實在匪夷所思。
雖然TKConnect有了一些聚合商支持,但是顯然遠未到說能夠取代GDS的地步。中國古話講「韜光養晦,厚積薄發」——在自身NDC平臺不夠強大的時候,還是不要提「取代GDS」為好;但是,在如今看來,NDC還遠未到能夠取代GDS的時候。
但是NDC的普及,某種程度上陷入了僵局——NDC好不好?好。技術上而言,確實解鎖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代理和GDS的商業模式,是有存在的合理基礎的;同時,NDC實施要成本的。
航空公司要想挑戰這種模式,要么就得擔下額外的成本,要么就得給出一個成本更低的解決方案,要么就得憑著自己的議價權,把成本轉嫁給代理人和消費者。
目前看來,航空公司三者都做不到:第一點來看,航空公司即使可以擔下自建服務端的成本,客戶端的成本也沒法承擔;NDC的學習曲線使得其成本并不比GDS低,為代理人增加新的負擔;單一航空公司的議價權也不足以讓代理人和消費者承擔。
因此,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航空公司銷售都會在GDS和NDC雙軌并行的路徑上走很久。
我個人的建議是航空公司把自己的產品這樣力所能及的事情先搞好,不要去搞渠道這種茲事體大,虛頭八腦的東西,搞到最后折騰代理人和旅客一地雞毛,事情灰頭土臉回到原點不說,自己的市場份額還給別人吃了,不值得。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退出登錄
退出登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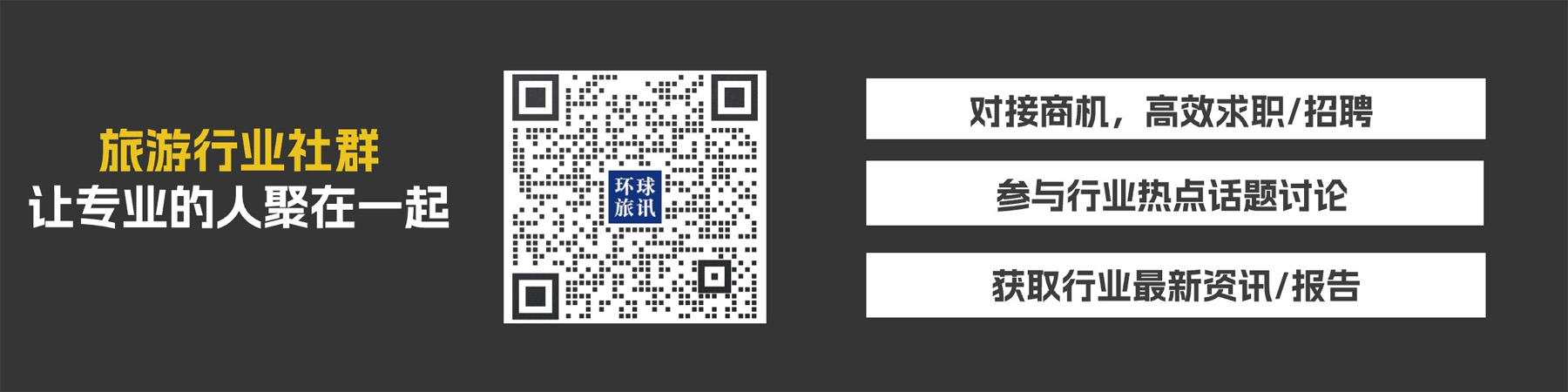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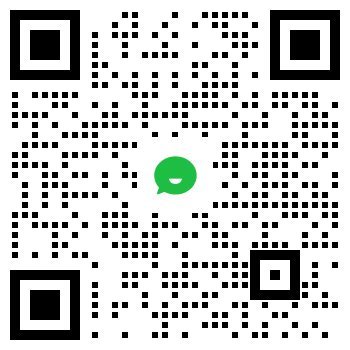





評論